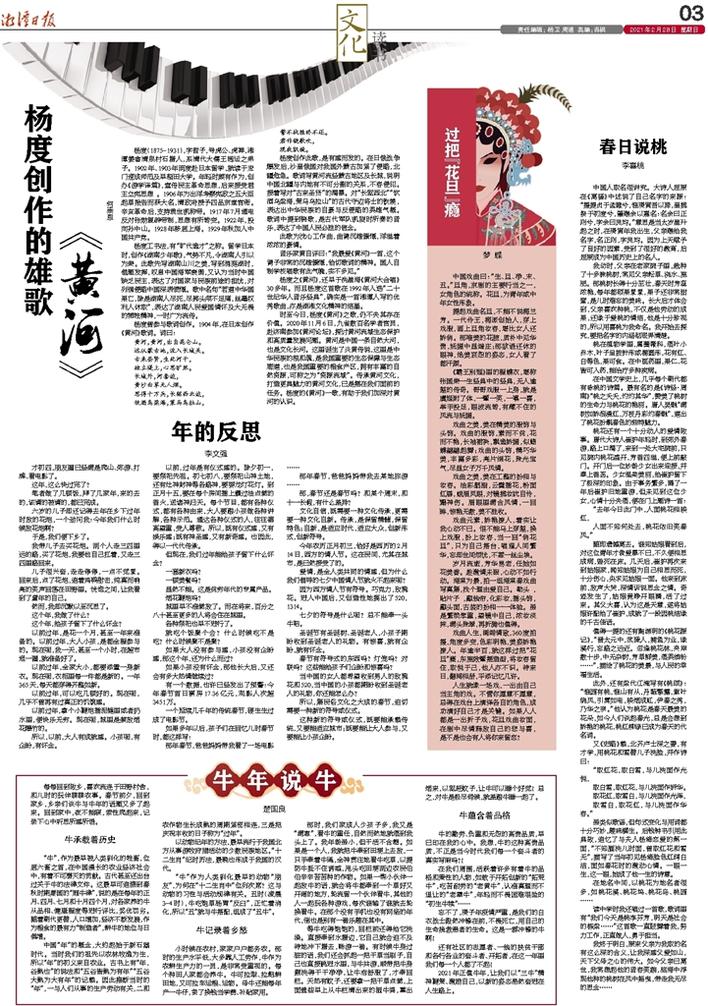才初四,朋友圈已经满是爬山、郊游、打牌、看电影了。
这年,这么快过完了?
笔者做了几顿饭,拜了几家年,来的去的,该请的被请的,都已完成。
六岁的儿子却还记得去年在乡下过年时放的花炮,一个劲问我:今年我们什么时候放花炮啊?
于是,我们便下乡了。
我带儿子去买花炮。两个人走三四里远的路,买了花炮,我要他自己扛着,又走三四里路回来。
儿子很兴奋,走走停停,一点不觉累。回来后,点了花炮,追着鸡鸭射击,纯真而响亮的笑声回荡在田野里。恍惚之间,让我看到了童年的自己。
然而,我却沉默以至沉思了。
这个年,我做了什么?
这个年,给孩子留下了什么怀念?
以前过年,是花一个月,甚至一年来准备的。以前过年,大人小孩,是都全程参与的。现在呢,我一天,甚至一个小时,在超市逛一圈,就准备好了。
以前过年,全家大小,都要添置一身新衣。现在呢,衣柜里每一件都是新的。一年365天,每天都穿得齐整如新。
以前过年,可以吃几顿好的。现在呢,几乎不曾再有过真正的饥饿感。
以前过年,拿个小鞭炮插泥缝里或者扔水里,便快乐无穷。现在呢,城里是禁放烟花爆竹的。
所以,以前,大人有成就感。小孩呢,有企盼,有怀念。
以前,过年是有仪式感的。除夕初一,要祭祀先祖。初七初八,要祭祀山神土地,还有灶神财神等各路神,要耍龙灯花灯。到正月十五,要在每个房间插上蘸过油点燃的香火,送诸神归天。每个节目,都有各种仪式,都有各种由来,大人要跟小孩做各种讲解,各种示范。通达各种仪式的人,往往德高望重,受人尊敬。所以,既有仪式感,又有娱乐感;既有神圣感,又有新奇感。也因此,得以一代代传承。
但现在,我们过年能给孩子留下什么怀念?
一套新衣吗?
一顿美餐吗?
显然不能。这是贫穷年代的专属产品。
烟花鞭炮吗?
城里早不准燃放了。而在将来,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的人将会住在城里。
各种祭祀也早不进行了。
就吃个饭聚个会?什么时候吃不是吃?什么时候聚不是聚?
如果大人没有参与感,小孩没有企盼感,那这个年,还为什么而过?
如果小孩没有怀念,那他长大后,又还会有多大热情继续过?
有一个数据,也许已经发出了预警:今年春节首日票房17.36亿元,观影人次超3451万。
一个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春节,硬生生过成了电影节。
如果多年以后,孩子们在回忆儿时春节时,都这样写:
那年春节,爸爸妈妈带我看了一场电影……
那年春节,爸爸妈妈带我去某地旅游……
那,春节还是春节吗?和某个周末,和十一长假,有什么差异?
文化自信,既需要一种文化传承,更需要一种文化自新。传承,是保留精髓,保留特色;自新,是适应时代,适应大众,创新形式,创新符号。
今年农历正月初三,恰好是西历的2月14日,西方的情人节。这在民间,尤其在城市,是已然接受了的。
爱情,是全人类共同的情感,但为什么我们倡导的七夕中国情人节就火不起来呢?
因为西方情人节有符号。巧克力,玫瑰花。进入中国后,又创造性地搞出了520,1314。
七夕的符号是什么呢?总不能牵一头牛吧。
圣诞节有圣诞树、圣诞老人,小孩子期盼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。有惊喜,就有企盼,就有怀念。
春节有符号式的东西吗?灯笼吗?对联吗?这些能给孩子们企盼和惊喜吗?
当中国的女人都希望收到男人的玫瑰花和520,当中国的小孩都期盼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,你还能怎么办?
所以,集民俗文化之大成的春节,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符号或仪式。
这种新的符号或仪式,既要能承载传统,又要能适应城市;既要能让大人参与,又要能让小孩企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