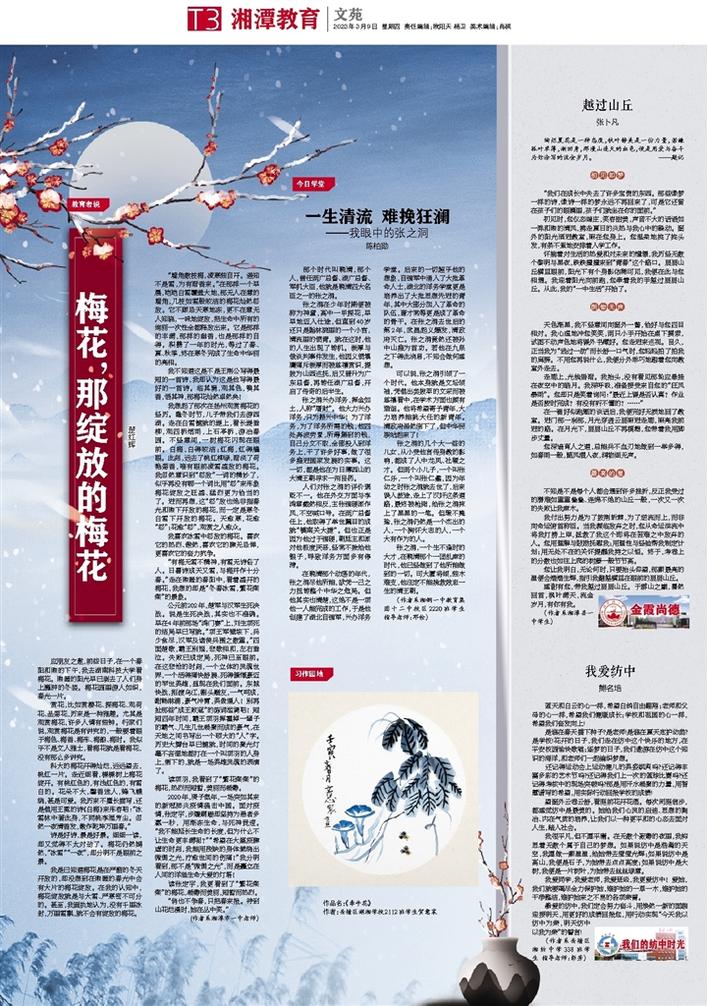应朋友之邀,前些日子,在一个春阳和煦的下午,我去湖南科技大学看梅花。煦暖的阳光早已剥去了人们身上臃肿的冬装。梅花园里游人如织,春光一片。
赏花,比如赏樱花、探梅花、观荷花、品菊花,历来是一种雅趣。尤其是观赏梅花,许多人情有独钟。行家们说,观赏梅花是有讲究的,一般要着眼于梅色、梅香、梅形、梅韵、梅时。我似乎不是文人雅士,看梅花就是看梅花,没有那么多讲究。
科大的梅花开得灿烂,远远望去,桃红一片。走近细看,棵棵树上梅花绽开。有桃红色的,有浅红色的,有雪白的。花朵不大,馨香迷人,蜂飞蝶绕,甚是可爱。我历来不擅长描写,还是借用王冕的诗《白梅》来形容吧: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
诗是好诗,景是好景。细细一读,却又觉得不太对劲了。梅花仍然嫣然,“冰雪”“一夜”,却分明不是眼前之景。
我是已知道梅花是在严酷的冬天开放的,却没想到在煦暖的春光中会有大片的梅花绽放。在我的认知中,梅花绽放就是与大雪、严寒密不可分的。甚至,我固执地认为,没有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,就不会有绽放的梅花。
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在那样一个早晨,皑皑白雪覆盖大地,那无人在意的墙角,几枝如雪般皎洁的梅花灿然怒放。它不顾忌天寒地冻,更不在意无人知晓,一味地绽放,把生命中所有的绚丽一次性全都释放出来。它是那样的丰满,那样的幽香,也是那样的自得。积攒了一年的时光,等过了春、夏、秋季,终在寒冬完成了生命中华丽的亮相。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王荆公写得最短的一首诗,我却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首诗。临其境,观其色,嗅其香,悟其神,那梅花灿然卓然矣!
我想起了那次在扬州观赏梅花的经历。隆冬时节,儿子带我们去游西湖。走在白雪铺就的堤上,看长堤垂柳,观四桥烟雨,上石亭桥,游冶春园。不经意间,一树梅花闪现在眼前。白梅,白得皎洁;红梅,红得耀眼。此刻,远去了桃红柳绿,暗淡了荷艳菊香,唯有眼前凌雪盛放的梅花。我忽然意识到“怒放”一词的精妙了,似乎再没有哪一个词比用“怒”来形象梅花绽放之旺盛、猛烈更为恰当的了。进而再想,这“怒”放也绝非指春光和煦下开放的梅花,而一定是寒冬白雪下开放的梅花。天愈寒,花愈“怒”;花愈“怒”,观赏之人愈众。
我喜欢冰雪中怒放的梅花。喜欢它的热烈、傲然,喜欢它的肆无忌惮,更喜欢它的奋力抗争。
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,与梅并作十分春。”走在煦暖的春阳中,看着盛开的梅花,我想的却是“冬春冰雪,繁花粲粲”的景象。
公元前202年,楚军与汉军生死决战。说是生死决战,其实也不准确。早在4年前那场“鸿门宴”上,刘生项死的结局早已写就。“项王军壁垓下,兵少食尽,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”四面楚歌,霸王别姬,悲歌相和,左右垂泣。失败已成定局,死神已至眼前。在这悲怆的时刻,一个立体的灵魂世界,一个活得痛快舒展、死得慷慨豪迈的罕世英雄,显现在我们面前。东城快战,拒渡乌江,割头赠友,一气呵成,酣畅淋漓,豪气冲霄,英俊逼人!别再扯那些“成王败寇”的陈词滥调吧!短短四年时间,霸王项羽挥霍掉一辈子的霸气、几生几世凝聚而成的豪气,在天地之间书写出一个硕大的“人”字。历史大舞台早已铺就,时间的聚光灯毫不吝啬地都打在一个叫项羽的人身上,剩下的,就是一场英雄灵魂的表演了。
读项羽,我看到了“繁花粲粲”的梅花,热烈而短暂,美丽而凝静。
2020年,庚子鼠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袭击中国。面对疫情,张定宇,步履蹒跚却坚持为患者多赢一秒, 用渐冻生命,与死神竞速。“我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,但为什么不让生命更丰满呢?”“希望在大瘟疫肆虐的时刻,我能用残缺的身体燃烧出微弱之光,疗愈世间的伤痛!”我分明看到,那不是“微弱之光”,而是矗立在人间的洋溢生命大爱的灯塔!
读张定宇,我更看到了“繁花粲粲”的梅花,凝静而美丽,短暂而热烈。
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,她在丛中笑。”
(作者系湘潭市一中老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