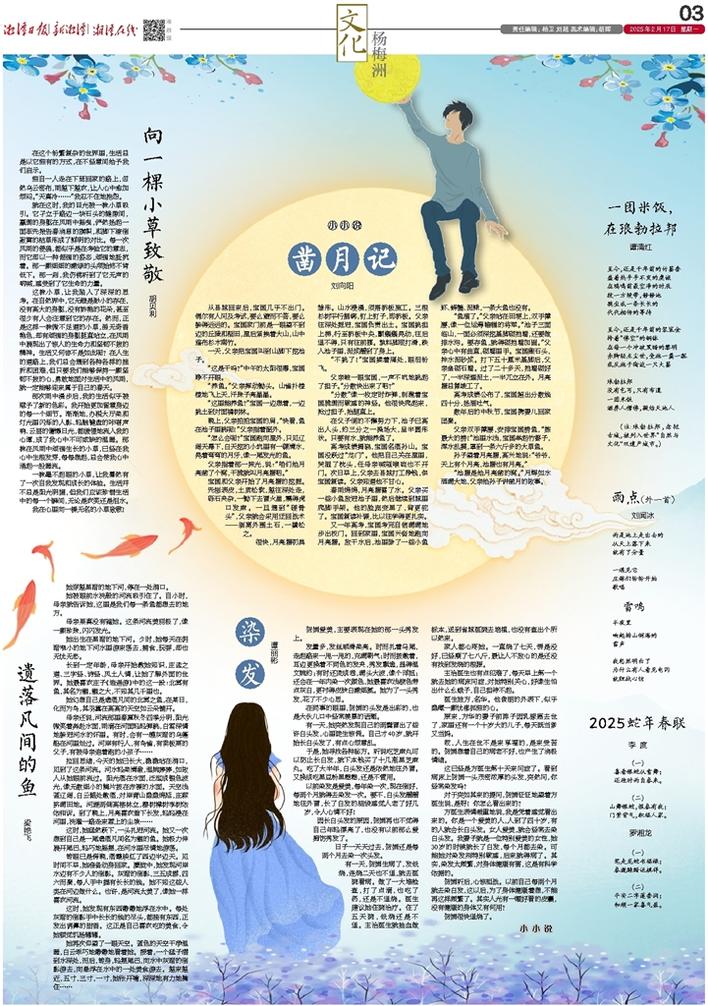从县城回来后,宝国几乎不出门。偶尔有人问及考试,要么避而不答,要么躲得远远的。宝国家门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和稻田,屋后紧挨着大山,山中遍布杉木南竹。
一天,父亲把宝国叫到山脚下挖池子。
“这是干吗?”中午的太阳很毒,宝国睁不开眼。
“养鱼。”父亲挥动锄头。山雀扑棱棱地飞上天,汗珠子亮晶晶。
“这里能养鱼?”宝国一边想着,一边挑土到对面橘树林。
晚上,父亲拍拍宝国的肩,“快看,鱼在池子里跳呢!”父亲指着窗外。
“怎么会呢?”宝国跑向屋外,只见辽阔天幕下,白天挖的小坑里有一碟清水,晃着弯弯的月牙,像一尾发光的鱼。
父亲指着那一抹光,说:“咱们给月亮凿了个窝,干脆就叫月亮塘吧。”
宝国和父亲开始了月亮塘的挖掘。先刨表皮,土质松软,越往深处走,砾石夹杂,一锄下去冒火星,震得虎口发麻。一旦遇到“硬骨头”,父亲就会采用迂回战术——剥离外围土石,一撬松之。
很快,月亮塘初具雏形。山水浸漫,须搭桥板施工。三根杉树平行捆绑,钉上钉子,即桥板。父亲往深处掘进,宝国负责出土。宝国挑担上梯,行至桥板中央,颤巍巍晃动,往后退不得,只有往前挪。孰料脚底打滑,跌入池子里,泥浆蹭到了身上。
“不挑了!”宝国揉着痛处,眼泪纷飞。
父亲睃一眼宝国,一声不吭地挑起了担子。“分数快出来了吧?”
“分数”像一枚定时炸弹,刺激着宝国脆弱而敏感的神经。他很快爬起来,抢过担子,抬腿直上。
在父子俩的不懈努力下,池子已高出人头,约三分之一操场大,呈半圆形状。只要有水,就能养鱼了。
高考成绩揭晓,宝国名落孙山。宝国没跃过“龙门”。他把自己关在屋里,哭湿了枕头,任母亲喊哑喉咙也不开门。次日早上,父亲去县城打工挣钱,供宝国复读。父亲知道他不甘心。
春雨绵绵,月亮塘蓄了水。父亲买一些小鱼放进池子里,然后继续到城里爬脚手架。他的脸庞变黑了,背更驼了。宝国复读补课,比以往学得更扎实。
又一年高考,宝国考完自信满满地步出校门。回到家里,宝国兴奋地跑向月亮塘。放干水后,池里除了一些小鱼虾、螃蟹、泥鳅,一条大鱼也没有。
“鱼溜了。”父亲站在田埂上,双手撑腰,像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。“池子三面临山,一面必须深挖基脚砌挡墙,还要做排水沟。要存鱼,就得砌挡墙加固。”父亲心中有曲直,砌墙里手。宝国搬石头,拌水泥砂浆。打下五十厘米基脚后,父亲垒砌石墙。过了二十多天,挡墙砌好了,一半深埋泥土,一半兀立在外。月亮塘总算竣工了。
高考成绩公布了,宝国超出分数线四十分,扬眉吐气。
数年后的中秋节,宝国携妻儿回家团聚。
父亲双手撑腰,安排宝国捞鱼,“拣最大的捞!”池里水浅,宝国举起竹篓子,浑水乱摸,罩到一条六斤多的大草鱼。
孙子望着月亮塘,高兴地说:“爷爷,天上有个月亮,池塘也有月亮。”
“池塘是给月亮凿的窝。”月辉如水洒满大地,父亲给孙子讲凿月的故事。